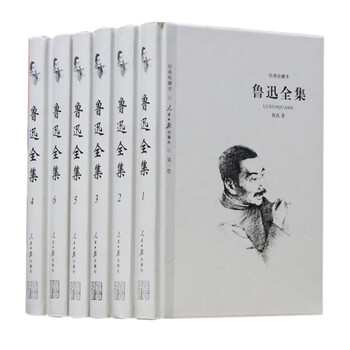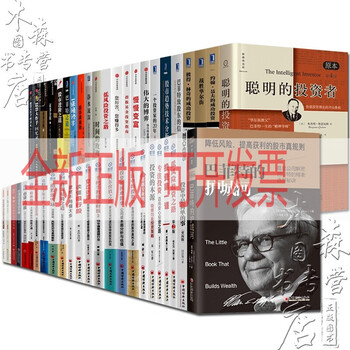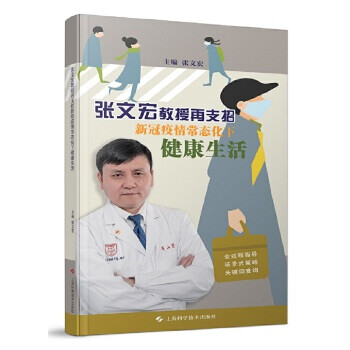《国史大纲》是一部中国通史,力求简要,举其大纲,删其琐节。在不到1000页的篇幅里,其人物之详、事业之备,又显示了作者驾驭繁复历史的伟力,整书纲举目张,简繁得当。《国史大纲》纵论中华传统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之演变发展,兼及中外形势,以求我国家历史之通贯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阐其一脉相承之统系,指陈吾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钱穆先生著述本书于抗战期间,在国家危亡中,读书人以笔为戎,以“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为著述之深厚根基,洋洋洒洒近80万言,荡气回肠,以激扬国人之民族精神,因应现实,更作为抗战建国之镜鉴。
《国史大纲》著于抗日战争时期。其时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疑古之论甚嚣尘上,同期新文化骁将钱玄同甚至于认为应该废除汉文。当此之际,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家国命运、民族未来的思考贯穿于全书。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于北大讲授通史课时,“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不骋空谈。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钱穆此一远大追求,终至大成于《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脱胎于授课讲义,但编撰时的立意已不限于教科书。《国史大纲》对国史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士族阶层追溯其历代变迁轨迹,以凸显中国史特色所在。
钱穆写《国史大纲》,遍读同期史学专家研究文字,根据他自己的通史观点而判定其异同取舍。《国史大纲》惜墨如金,语多涵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的旧史料,实则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
严耕望将《国史大纲》读了好几遍,越读越倾佩:“早年我即钦服宾师境界之高,识力之卓,当上追史迁,非君实所能及。再读此书,此信益坚……即此讲义,已非近代学人所写几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项背,诚以学力才识殊难兼及!”
“上追史迁”毫无疑问是至高评价,“学力才识”则道出了钱穆治史过人之处的原因所在。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一节是《国史大纲》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为了编撰这一节,钱穆的数据考据极为扎实。经济方面参考了唐朝天宝年间仓粟、元代岁入粮数、唐十道贡赋丝布织物、洪武年间夏税绢数等各项数据,文化方面参考了唐会昌年间进士数、明朝乡试及会试额数、宋元明户口数等大量史学研究数据,依此数据考据,钱穆得出:“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吕思勉盛赞《国史大纲》论南北经济这一节,还说《国史大纲》写魏晋屯田到唐代的租庸调,自古至今进行史学研究的人,没有人能像钱穆这样能“详道其所以然”。
吕思勉对整本书的评价是“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作为中国通史的大师、钱穆的师长,吕思勉的这一评价是极高的了。
《国史大纲》开篇即谓“温情与敬意”,旨在唤醒国人的民族自信:“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钱穆首倡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应仅限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之责任,“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此即“温情与敬意”的本意。阅读《国史大纲》,时时体会到钱穆所倡之“国家民族独特精神”: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中国文化和历史独特精神”不止钱穆的学术观点,实为钱穆一生不移的信仰。余英时在《师友记往》也有此论:
梁启超、章炳麟、《国粹学报》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钱先生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这一点无疑是承清末的学风而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承继了清末学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接受他们的答案。他的一生便是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径。《国史大纲.引论》所说的“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正是这一路径的具体描写。但这在他不是空论,而是实践。
阅读《国史大纲》推荐纸质书,纸质书正文以大、中、小三种字体排版,大字体为正式内容,中字体为引用的史料内容,混排于大、中字体之间的小字体为钱穆的注释。三种字体编排有序,清晰明了,阅读时不需来回翻阅,极为方便。
《国史大纲》出版之后,因其境界之高、议论之卓,被当时学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最佳著作。八十年后的今天,阅读时仍能感受到钱穆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对“中国文化、历史自有精神”的信仰。
余英时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是一部应该人手一编的中国史学无尽藏”,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