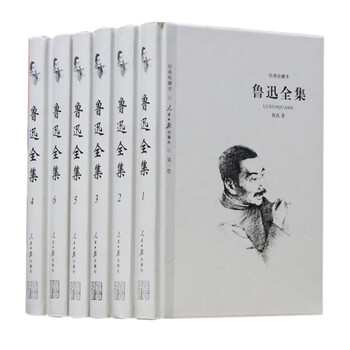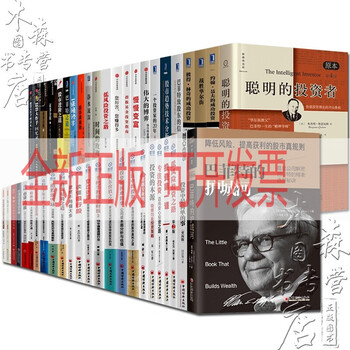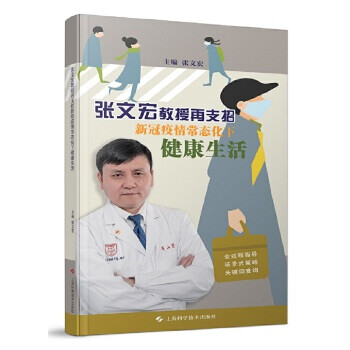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人类学家常常把它们作为人类早期演进的三大阶段,那么,我们当然早已进入文明,而且千万年下来,早已进入一种充分成熟的文明。我们的一切举止作为,好像应该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
读罢游记《千年一叹》后,再读余秋雨先生的《文明的碎片》,颇有一番感受,近年来读过很多的散文大家的作品,老舍的,梁实秋的,周作人的,汪曾琪的,冰心的,季羡林的,朱自清的,台湾作家席慕容的,龙应台的,历数散文大家,睿文以自己的审美情趣倒是比较喜欢梁实秋的散文与余秋雨的作品,梁实秋的作品于细微处见精神,能提升一个人的思想高处与看人情世故的特殊视角,特别是他与文艺界的名人过往,可以佐证一些相关的史实,而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则从大处着眼,洞察事物的机理,道出深层次的潜藏,这是一个人的大智慧,见微知著才是一个作家本应拥有的领悟力。
余秋雨先生文学功力可以用“不同凡响”来概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 《行者无疆》 《晨雨初听》 《借我一生》 《笛声何处》《寻觅中华》《摩挲大地》,这样的提纲挈领,就有了诗词的韵味、国学的美感。读来常常令人怦然心动,掩卷长思,
本书《文明的碎片》共收集了二十五个章节,一个题叙,一个附录,一个注释,而二十五个章节,如《道士塔》、《阳关雪》、《西湖梦》、《笔墨祭》、《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等都情凝笔端,洋洋洒洒,读来令人酣畅淋漓。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的力量和精粹。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如此的认知,就如航标灯一般指引着读者去去审视废墟所承载的历史,所彰显的历史脉络,今日大众所应给予的人文关怀。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含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轻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
“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这是那个时代走来的人们并不知道的政治制度的深层逻辑,可我们又偏偏会想起:“等贵贱、均贫富”这样的政治主张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政治纲领,当然这是人性丑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以文明的衣裳加以掩盖,才能使我们有一些体面,可这又能如何呢?熙来攘往的世人就这样一直前仆后继走了几千年,生生不息,而这一切又恰恰是政治家的死结,今日之世界分崩离析,各立山头,老子的大同世界又在资源争抢的扰攘中幻化成了泡影......
“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
“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
“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此由而生。”
这是该书第二十六章《都市良知》中对上海人的描述片断,非为睿文的断章取义,如果再读王安忆的《长恨歌》也许上海人的个性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更为贴切一些罢了,应该说,秋雨先生对上海人的群体性格、思想动态、世俗狡黠刻画地入木三分,对睿文而言,也许这份直观地理解更为深刻一些,更为理性一些,毕竟这是一 个特殊的群体,特殊到被除上海以外的人们所不能接纳,然而他们的“特殊光环”已渐渐淡去,成为孤岛上的鲁滨逊,只能靠自己的精明来救赎自己,今日国际大都市的繁华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创造的神话,以“小市民”的清高来孤立自己,无异于作茧自缚!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在该部作品中,秋雨先生用墨最多,不断地变换视角来审视上海人,这样的独具慧眼,不知今日中国作家中几人能够?这是沙里淘金式的客观理性,这是分辨稂莠的智慧,这是洞若观火的冷静。读来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