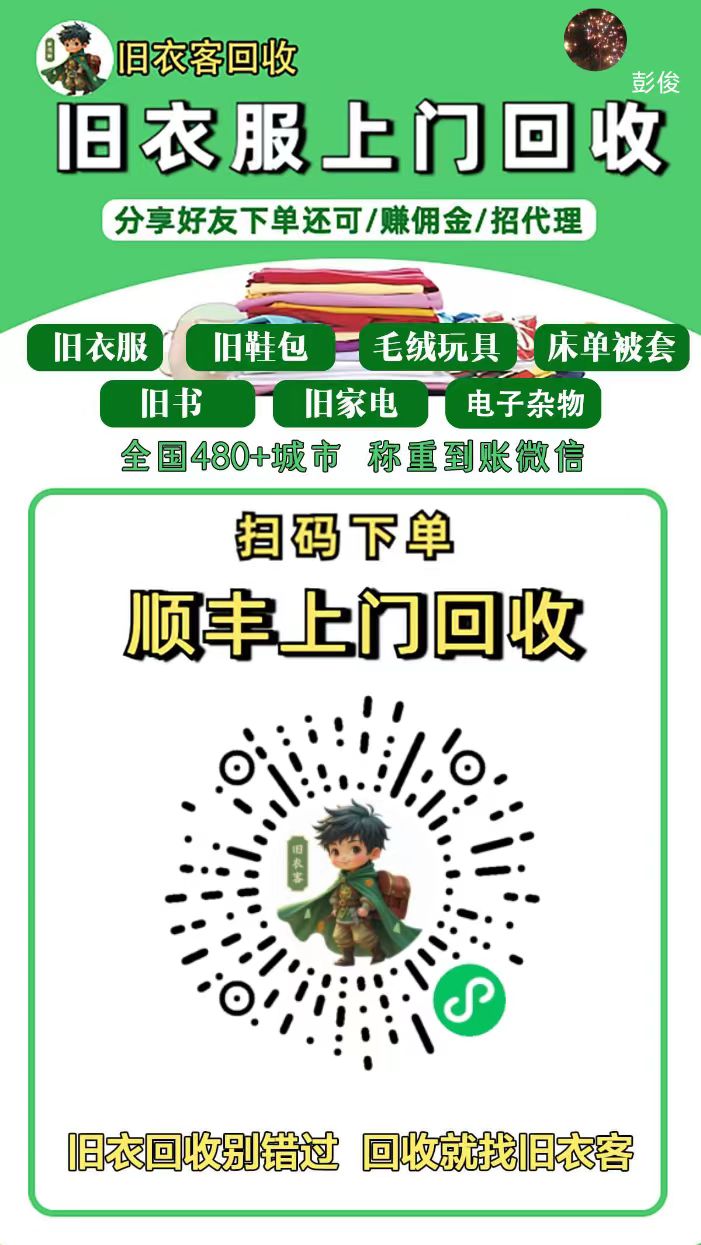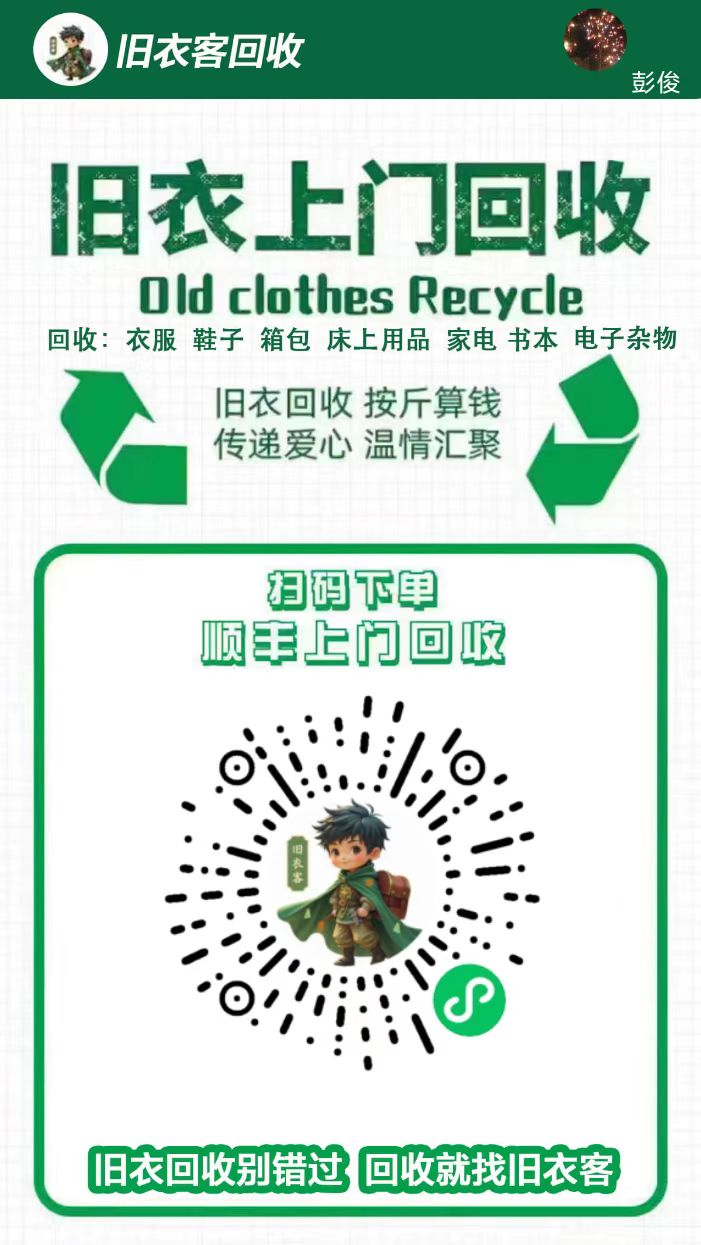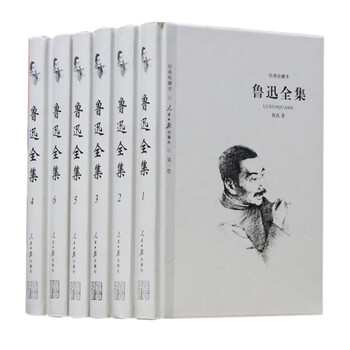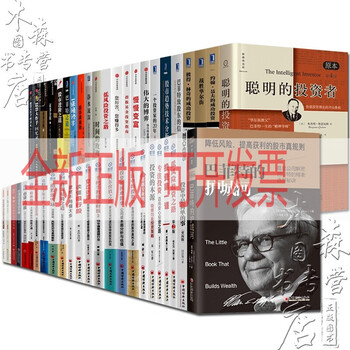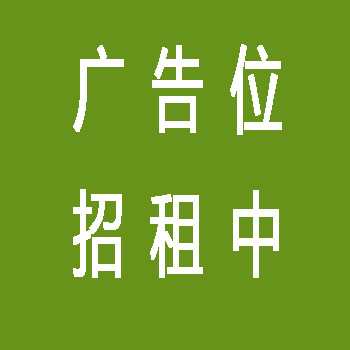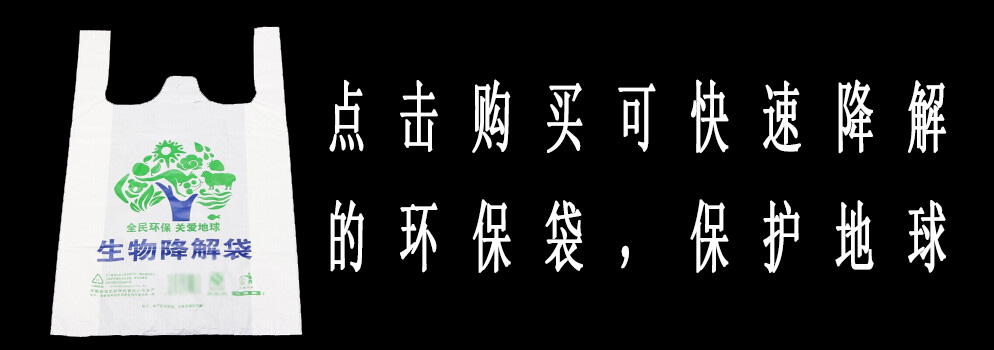“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一丽一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在早晨,她就是洛,普普通通的洛,穿一只袜子,身高四英尺十英寸。穿上宽松裤时,她是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丽。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这段文字来自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这是所有的小说里最美的开头,以至于我每次读的时候都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你一定听过一个词,“萝莉”,指可爱的小姑娘,这个词就来自于这部小说
这是一个非常受争议的小说,1954年刚完稿美国好几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后来的几十年间,也曾经被各个国家出版拒绝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部太挑战我们作为读者的道德的一本书: 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个恋童癖。
小说是以主角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在小说的开头,他已经作为犯罪分子被抓起来了,整个小说就是他的自我辩护书。
我就以第一人称来复述这个故事:“我”,亨伯特到底犯了什么罪?
亨伯特在13岁时,疯狂爱上了12岁的安娜贝尔,但她很快死于风寒,这件事在主角心中留下了永恒的伤痛,给他留下了病态的爱好——我喜欢9岁到14岁之间某一类小女孩。我曾经娶过一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喜欢模仿小女孩
37岁,我遇到一个12岁的少女。当我第看到她我把她闪光的美丽每一处细节都吸进我的眼里,和我记忆里死去的爱人安娜贝尔对比,但我发现她不是安娜贝尔,她是一个新的更好的人,她是我的洛丽塔。
主角得到了和洛丽塔独处的机会,得到了她在夏令营里学下流节目。从那以后,主角驾车带着洛丽塔周游美国,后来把她送进了当地的女子学校,这可能是主角犯过最大的错误,因为洛丽塔忽然失踪了
几年之后,收到了洛丽塔的信,说自己已经结婚怀孕了,需要钱。在贫民窟找到了她,洛丽塔已经变得憔悴不堪,她给“我”讲了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原来她当时被一个剧作家拐走了,那个剧作家比亨伯特更变态,甚至更早和洛丽塔发生了关系。拐走洛丽塔之后,剧作家强迫她拍色情电影,洛丽塔拒绝之后被抛弃了,嫁给一个贫穷残疾的退伍军人,怀了孕。
离开亨伯特的洛丽塔之后,亨伯特满脸泪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找到了那个剧作家,以洛丽塔父亲的名义,用一把手枪干掉了他。
现在,亨伯特在狱中写下我的自述。当你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亨伯特应该已经死了。
最后,亨伯特因为血栓死在狱中,17岁的洛丽塔在几个月后死于难产。
亨伯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讲述者,我们听得入神。他时而温柔,时而残忍,时而斥责自己是恶魔,时而又试图告诉我们,他变态,是因为他的爱太强烈了,他爱洛丽塔胜过他见过他想象得到的一切,他在小说结尾,要求怀孕的洛丽塔给他一起走,被拒绝之后,他还是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了洛丽塔。
在听亨伯特的讲述时,有一种奇妙的感受,觉得亨伯特是在替我们所有人说话,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这样情欲的火焰,但是被压抑住了,而亨伯特活得比我们更纯粹,对自己的欲望更诚实;我们中的一部分人陷入不那么道德,或者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恋爱,那种恋爱像是共谋一样,两个人心照不宣,无法向世人诉说,只有亨伯特如此坦诚地去公之于众。
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们就不断被矛盾的情绪撕扯:
到底该如何看待亨伯特?如何看待《洛丽塔》?纳博科夫到底想说什么?
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本小说讲的不是一个狡猾的成年人去让小女孩堕落的故事,而是一个已经堕落的儿童去玩弄一个软弱的老男人的情欲。
评论家的想法是从亨伯特的叙述中得来的,亨伯特说:我一直小心不想破坏洛丽塔的清白,是小女孩提议我们做下流的事;亨伯特还似乎不经意地指出洛丽塔的庸俗、冷漠、无礼、自恋,根本就不珍惜亨伯特对他的爱,只是想用自己的魅力从他那里换点好处。
所以评论家说说这个故事讲的不是道德,亨伯特是个可怜的人,他被自己的情欲蒙蔽了,不断去美化这个普通的姑娘,就像夸父逐日一样,追逐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甚至为了她而死去。如果说亨伯特有什么罪的话,就是他放任自己被爱情折磨。如果说亨伯特有什么错的话,就是他太诚实了,他对自己的欲望太诚实了,以至于没办法被世人所理解。
这是《洛丽塔》这本书辩护者的观点
你是不是也被这种说法说服了,我们需要去理解他,因为文学是为了展现人性广泛的维度—甚至包括最幽暗的那些。我们也应该诚实地接受自己那些幽暗的欲望。
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成功地上钩了,你上当受骗了,你被亨伯特骗了,你也被纳博科夫骗了。
纳博科夫写《洛丽塔》,根本不是想让我们理解一个恋童癖,理解人性的幽暗之处。恰恰相反,纳博科夫是想我们警惕这个变态。
整个小说都是亨伯特的自我辩白。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故事的一切认知都是建立在亨伯特的叙述上。
我们读小说的时候,总是会一开始就有代入到主角视角,我们看到的,经历的和主角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小说里讲的就是真的,我们不会去辨别叙述者撒了什么谎,或者隐瞒了什么。
在《洛丽塔》里,纳博科夫很厚道地在一开始提醒我们:这是犯人的自我辩护,而作为读者的你是陪审团,你要判断亨伯特的哪些说辞是在自我开脱。
所以这就给小说的阅读埋下了伏笔。
我认为纳博科夫是提醒我们要警惕亨伯特的,是纳博科夫自己评价亨伯特的时候说:
“这是一个自负、残忍的恶棍,却努力显得动人。‘’
亨伯特的人性并没有什么超常的地方,不像那些为这部小说辩护的文学评论家,认为他是一个格外纯粹,格外浪漫,格外疯狂的人。因为纳博科夫压根就不喜欢描写这种人性。
在《俄罗斯文学讲稿》里,纳博科夫说自己非常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为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都是精神病。
他觉得小说中那些病态、扭曲的灵魂所作出的反应,已经不再是人类的反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过于变态,尽管作者想通过这样怪人所作的反应来解决他提出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
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大家都要在医学上做研究,攻克一种病,要弄清楚人体构造,因此需要解剖人体,这时候你解剖一只穿山甲,虽然很刺激,得到的造型很奇特,但是并没有什么意义。
在纳博科夫看来,亨伯特只是一个可悲的普通人,他唯一的超常之处就是巧言令色,因此他努力用语言为自己开脱,努力去夸大自己的人性。去把他对少女的暴行,按照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去解读。警醒我们不要夸大恶的深度和美感,不要把它提高到它配不上的位置上。
亨伯特不断地推卸自己所造成的伤害,在小说的结尾,他杀了剧作家之后,在山谷里听到孩子玩耍的声音,他说“我明白了绝望的事情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被打动了,认为他忏悔了,灵魂升华了。其实亨伯特不是忏悔,他只是自我感动。
只有在洛丽塔已经不再是他发泄性欲的工具之后,他才允许自己反思;只有在出现了一个比他更恶劣的剧作家之后,他才会从灵魂上审视自己。可是,一个坏人杀掉另一个坏人,并不能洗清他本身的罪恶,时过境迁之后的悔恨也掩盖不了罪恶的本质——因为如果洛丽塔没有从他身边逃掉的话,他依然会牢牢地控制她,摧毁她的精神
我认为《洛丽塔》是在谴责亨伯特的证据,是纳博科夫赞美洛丽塔这个角色,说她是自己在小说中最崇拜的第二个人一第一个是普宁,是我特别喜欢的小说《普宁》中的角色。
如果洛丽塔仅仅是亨伯特口中那个除了年轻美丽,其他没什么特殊的女子,那么,纳博科夫为什么会崇拜他?
为什么纳博科夫崇拜洛丽塔?因为洛丽塔从亨伯特身边逃跑了,而且她并没有因为那几年的遭遇变成一个精神上完全堕落麻木的人。当剧作家让她拍摄色情电影,让她参加一些色情活动的时候,她断然拒绝,虽然承受了很大的代价
亨伯特和剧作家都是在某种意义上有魅力,有才华的人,但是她最后选择嫁给一个耳聋、贫穷的退伍士兵,士兵毫无才华,但洛丽塔非常坚决地要生下他的孩子,因为她想证明:所谓才华,所谓话语所编织的那些华丽的谎言,已经彻底无效了。
洛丽塔的这个选择让我想到前段时间讨论度很高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以自身经历为蓝本,讲一个未成年的少女是如何被老师诱奸,老师同样是以艺术的语言,充满魅力的话语去诱惑少女,而少女一方面被这种话术迷惑,另一方面因为这种经历太痛苦了,以至于必须合理化才能减弱痛苦,因此要说服自己其实是爱老师的。
但最后,作为主角的少女,也是作者醒悟了,她写到,老师虽然满嘴温良恭俭让,但是老师对“温良恭俭让”的解读是:
‘’温暖的是体液,良莠的是体力,恭喜的是初血,俭省的是保险套,让步的是人生。‘’
这才是华丽语言之下赤裸的本质,这才是丑陋的本质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中的洛丽塔也死了。但是在死之前,她们用尽全身的气力,去抵抗,去戳破了恶魔的谎言。
最后,我认为《洛丽塔》本质上是个道德故事,最有利的证据,其实是纳博科夫在信里写的,他说:
‘’当你认真阅读《洛丽塔》时,请注意,它是非常道德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部小说面对着非常讽刺的命运:一开始,它被禁,因为大众认为它是反道德的;后来,一批文人为它辩护,说它不是讲道德的,它讨论的是人性;但是纳博科夫自己说:这就是一部道德小说,而且是一部宣扬道德的小说。
这部小说真正道德的地方,其实不在小说里,而是在考验看小说的我们。作为读者的我们,作为陪审团的成员的我们。我们必须有非常强大的心灵,才能够戳穿亨伯特用语言布下的迷魂阵,坚持自己在一开始最朴素的道德判断。亨伯特是有罪的。
无论他显得多么有魅力,无论他说得多动听,他就是有罪的。
不仅在小说中,在生活中我们面对的这种考验更多。很多时候,我们被谎言所骗,为罪恶开脱,不是因为谎言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因为我们内心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角落,不愿意去面对的角落。
为他人的罪恶开脱,本质是为自己开脱。
但纳博科夫想说的是,去直视这些角落,去诚实地做判断。如果我们内心有针对自己的陪审团,请你不要对他们撒谎。请你想想洛丽塔,请你像她一样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