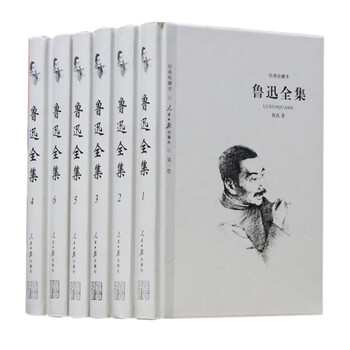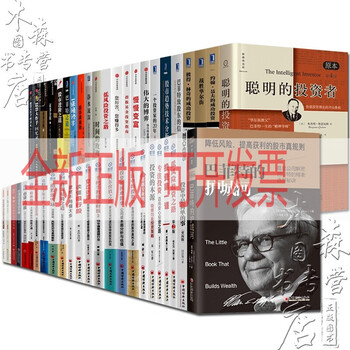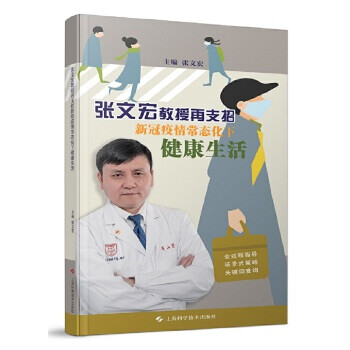张艺谋作品大多选择农村题材,这种乡村传统题材的把握,具有双重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是对苍凉、贫穷、残酷的反思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原始生命力的探求与赞叹。《红高粱》是以植物名称为题的,影片叙说了黄土地上“我奶奶”与酿酒汉子洒脱近乎狂荡的生活以及对抗日寇的野蛮侵略的故事,但是其中反复渲染的在风中起伏不倒的红高粱、漫天弥漫的黄土和一望无际的原野正是象征着中国西部大地上像红高粱一样淳朴的民风宽厚的习尚以及刚健不屈的精神。此时,张艺谋已不再满足对影片表层结构中故事情节的叙说,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影片内容的深层底蕴进一步开拓。
《菊豆》也是如此,表面上叙说了古老的染坊里男女情爱生儿育女的恩恩怨怨,杨金山、杨天青死在了染池里,菊豆烧死在染坊,站起来却是染坊里长大的封建思想守护神杨天白,是他杀死了他的爹娘,染坊已不只是染黑了一匹匹白布,而是连人的思想精神都染黑了。此时,染坊的故事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现实存在,更重要的是其中蕴涵的象征色彩:中国封建文化是个大染池,谁生于其中,谁都将受污染。这是主题的象征意义所在。
人物象征是张艺谋电影导演的创新,他选择的人物身上,都带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在人物的选择上,张艺谋选择女性作为主要的人物,她们身上就象征着一种坚韧、执着、内敛的温情主义。但是,这些人物却又不是真正的中国女性最合适的象征,她们的肉体、精神及心理上积淀了浓重的反道德、反理性等反封建传统意识,她们弱势群体的身份本身与这种反叛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为强烈的对比效果,因而更具有象征意味。
这些女性在张艺谋看来都具神性,近乎完美,因此昭示着生命的回归。他选择女性,借
用女性的性别特征,阐释其因性别带出的人性内涵,特别关注其中有关生存繁衍等生命现象。在人物的塑造上,张艺谋的创新也是与众不同,以传统的艺术眼光看来,电影应该在有限的时空内揭示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命运,以人物为中心罗织故事演绎情节,但是,在张艺谋的影片中,许多人物被省去了性格发展的逻辑程序,他把人物变成了凝固的雕塑,这就是导演苦心营造的象征天地,他把人物作为符号,去承载某一文化因子,去体现作品的主题。如《菊豆》中,只有 3、4 岁的小天白看到母亲与别人幽会时,竟脸色冰冷、怒目而视,似乎他一诞生的血液里已溶进了封建伦理文化的基因,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已根植了封建卫道士的种子。然而导演正是想通过这个人物符号说明中国封建文化的巨大侵蚀力,从而使影片的主题因这个人物得以昭显。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陈老爷,甚至在影片的整个过程中都有正面露过脸,观众看到的只是穿着一身黑衣的背影,听到的是严厉冷酷的声音。这样的人物在导演的观念中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充当一种理念的载体,在这个森严冷酷的高宅大院里虽然有他这个至高无上的君主统治着,但真正扼杀女人们的人性、青春与自由的,却是由这个人物符号象征蕴涵的夫权、贞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陈老爷只是个封建势力与思想的化身罢了,能否看到他的面容在影片中已不重要。
《活着》中的小男孩儿有庆虽是着墨不多,但却是颇令人深思的艺术形象。他看到有残疾的姐姐受人欺负,愤愤不平,只身一人勇敢地与一群孩子较量,并为此引来一系列麻烦,以最终受到父亲的训诫了事。有庆的举动是一个孩子出于纯朴自然的本能对人的尊严、自由、平等权益的一种维护,可父亲也是怕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不得不违心地教训儿子,一个充满自由独立意志的幼芽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中,从中透视出那个岁月专制魔爪的阴影已开始笼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