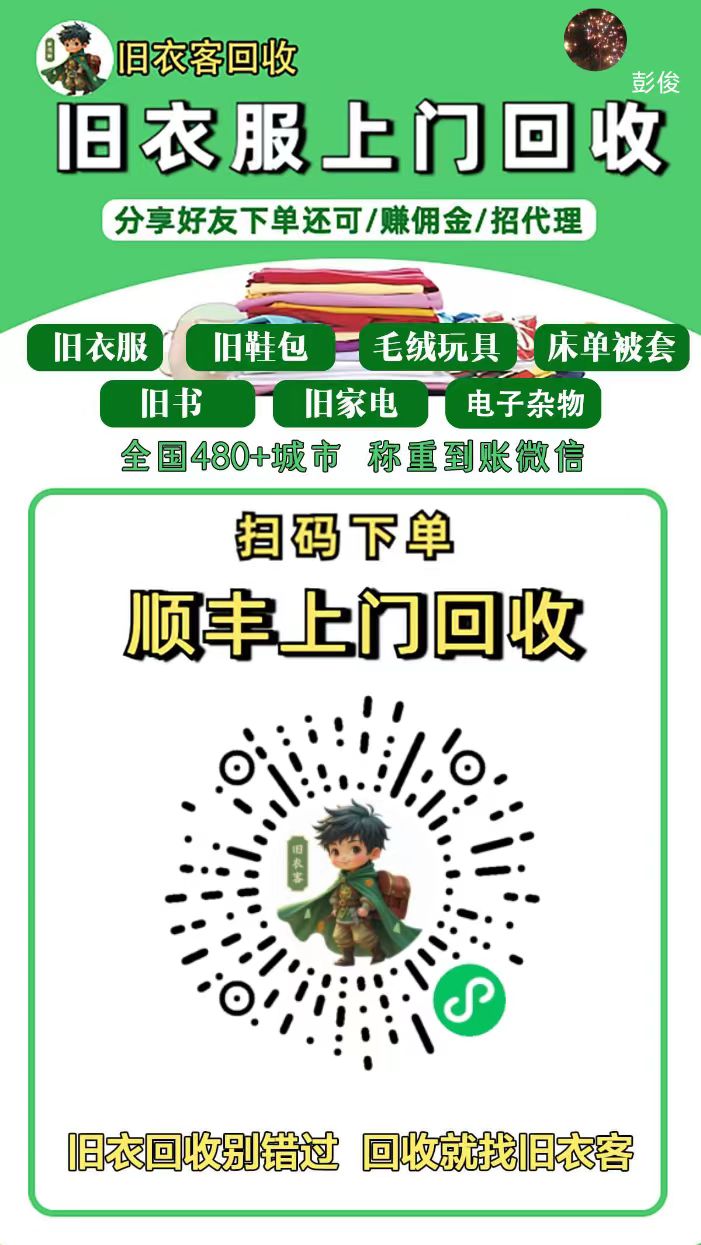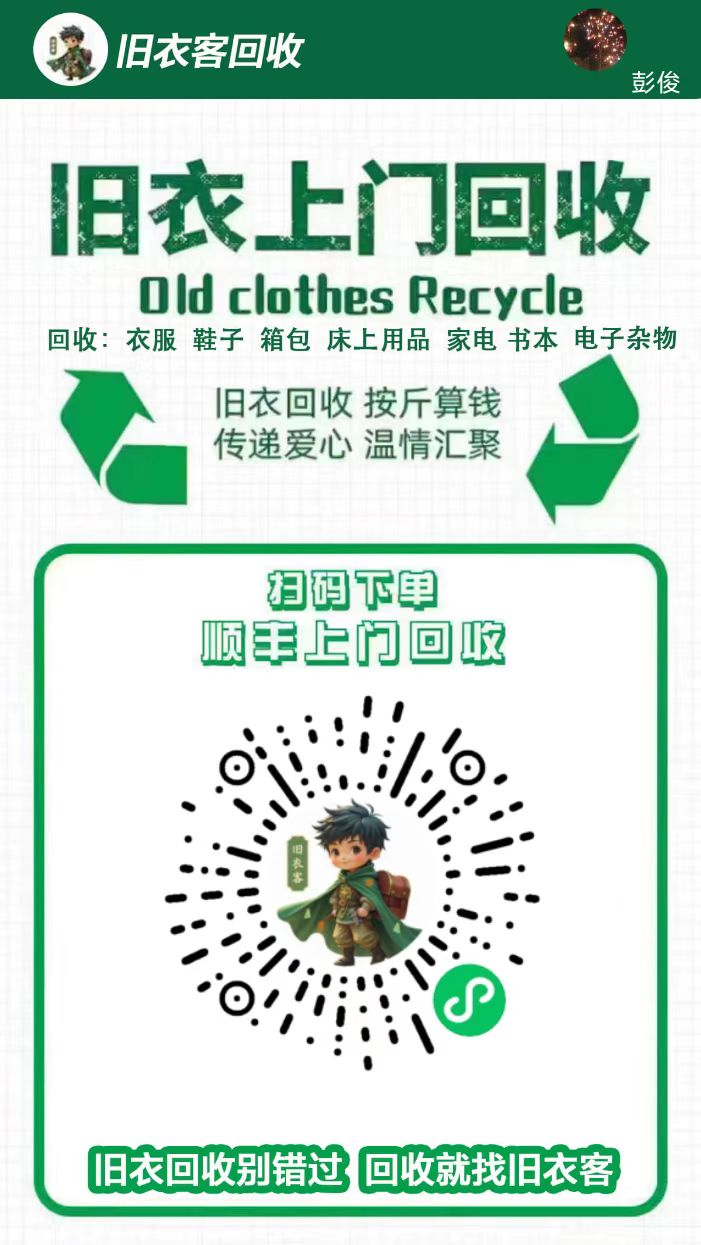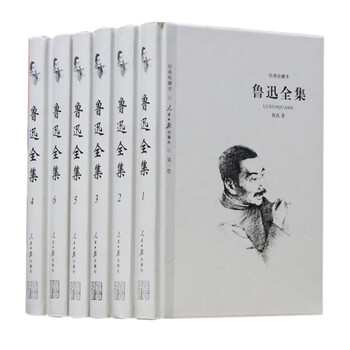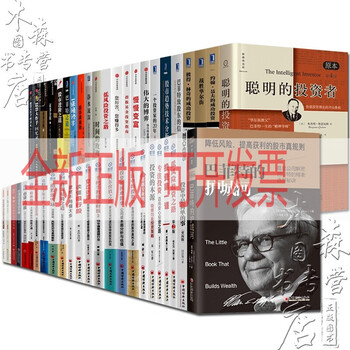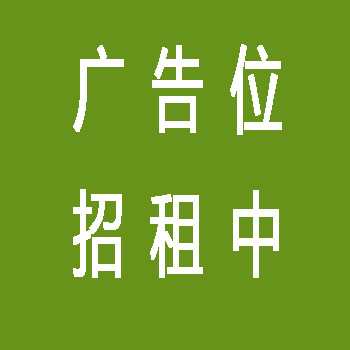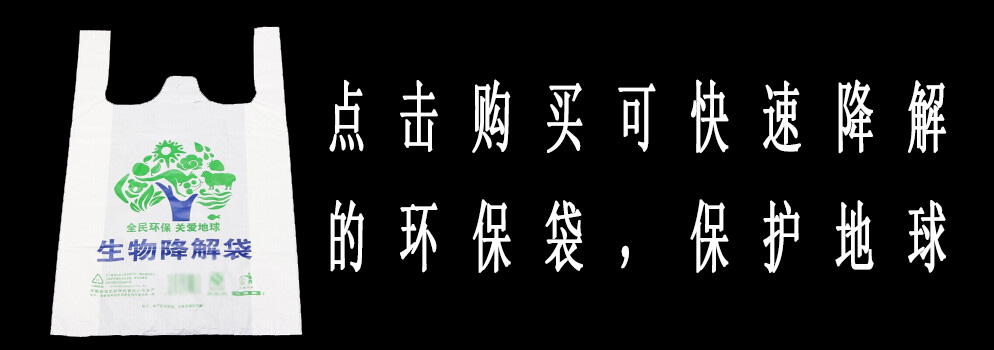常识杀死浪漫
上一次有这种拍案叫绝、忍俊不禁的感觉,还是在读《围城》的时候。同样是写婚姻世故,钱钟书的表达精巧老道,而老舍先生的语言个人特色突出,平实却又鲜明,京片儿,话赶话,都是人物内心的碎碎念,却并不叫你厌烦,念着念着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节奏紧凑,刻画起家长里短和社会群像更是鲜活生动、犀利幽默,且这种幽默通篇可拾,着实佩服,不愧是老舍先生自个儿最满意的作品。
如果说《骆驼祥子》写出了底层人物的命运如同被生活抽转的陀螺,那我觉得《离婚》则展示了庸俗社会学这个漩涡,如何将我们吞吸并同化。
文中的张大哥,是北平人的生存典范,圆滑世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什么事都热心张罗,“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他是弥漫着的“空气”,这空气并不是要毁灭老李,而是要同化格格不入的他;而老李在这空气中感觉窒息,“听着他们咕唧,好像听着一个臭水坑冒泡,心中觉得恶心”,却又渐渐觉得这空气自有它的馥郁芬芳,心中追求的诗意屡次冒出火花又被浇灭,这是浪漫主义向庸俗社会学举的白旗,是众多知识分子的矛盾和悲哀——一面批判着污浊的社会,一面又不得不被摁头妥协,拧巴着被同化。心中残存的诗意,要如何与狗血的现实、艰难的婚姻共存,是全文的主线,却始终没有答案。
“诗意”?世界上并没有这么个东西,静美,独立,什么也没有了。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
小说的结尾安排老李归隐回了乡下,感觉是作者给予浪漫主义的意志支持,正觉草率突兀,又来了张大哥一句——“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这是一句混账的断言,却又让人找不来底气反驳,悲哀至此又彻底了些。
浪漫主义理想就像玻璃,那么坚硬却又如此脆弱,叫人不禁惘然。多少不谙生存之道、社恐、拧巴的“老李”们,还在与生活的游戏规则较劲,与生活扭打。有时候想想,文学,就是我们在心中开辟出的田园,呵护“诗意”的微光,休憩整装,以便继续上路。